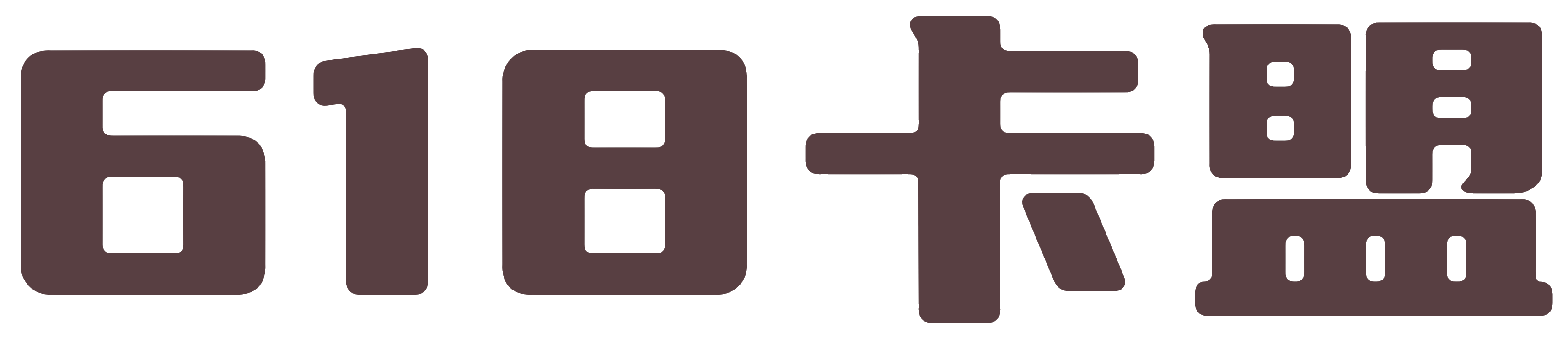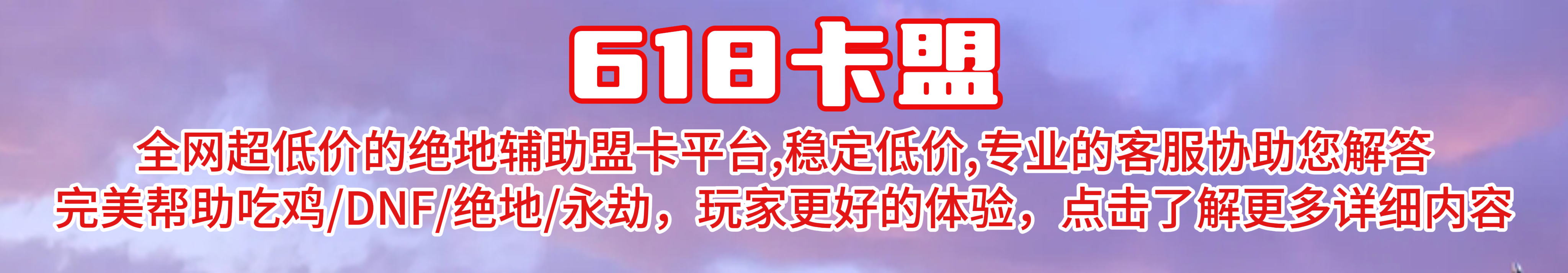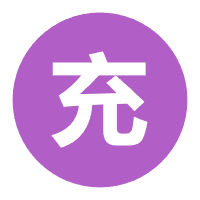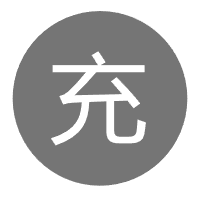家庭里的“游戏”之争
时隔半年,文洁还是常常想起,因女儿擅自给游戏充了三千多块,她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战场:丈夫打了女儿,女儿闹起了绝食。那一刻,她感觉好像“失去了女儿”。女儿也从此变得“好冷漠、好陌生”。
她将这些厄运归结为女儿沉迷于“游戏”。
在当下的中文语境里,“游戏”常常指向电子游戏。在中国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二十余年里,“游戏”屡遭“网瘾”“电子鸦片”等争议。
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这在互联网上被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政策”。
新规落地至今,关于“游戏”的争议仍在继续。

中国上海,一家网吧内,年轻人上网玩电子网络游戏。图源 IC photo
被改变的孩子
文洁不会忘记,从去年11月的一天起,她的生活遭遇突变。那天她随手查看微信的消费流水,发现自六月以来,共计有游戏支出3000余元。对她的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钱:她在湖北黄冈市的一农家乐做服务员,每天挣50元;丈夫则在工地做小工,收入也不稳定。
晚上回家,文洁问15岁、上初三的女儿小慧,最近是不是在打游戏?小慧说,偶尔打。她又问,充钱了吗?小慧说,是充了一点,但不知道充了多少。
文洁将手机上的账单甩在小慧面前,指责她不懂事。小慧一梗脖子,与她吵起来,“她说就是她充的,那又怎么样呢?”
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福建北部某乡村的张海宁家。2020年夏天,张海宁偶然查出,自己的一张银行卡在半年间有两千余元的游戏支出。他叫来10岁的儿子洋洋严问了一番,洋洋吞吞吐吐地承认,“一次充五十、一百的,充了许多次,还把扣费短信都删除掉了。”
从此,张海宁明令禁止儿子玩手机游戏,儿子口上答应,“实际上在想尽办法偷玩。”家里因此闹得鸡飞狗跳。
张海宁有两台退役的旧手机,虽不插卡,连着无线网络也能使用。为免儿子偷玩,他将旧手机藏在柜子里、罐子里、衣服里。但都被儿子翻出。儿子还会以读学校通知、查学科作业等理由要来手机。张海宁有事走开,半小时、一小时后回来,儿子称作业仍未查完。有几次,张海宁突击返回,逮到孩子正是在玩游戏。
“能怎么办呢?最多就是批评两句。”张海宁说,“小孩说有作业不会做,要用手机上网查,我总不能不给他查。”他唯一欣慰的是洋洋还算“乖巧”,被批评时,“就看看天,看看地,从不回嘴。”
文洁则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与女儿因游戏消费吵架的第二天,收工回家的丈夫听说事由,气得发抖,动手打了女儿。
家庭矛盾就此爆发。女儿绝食近一周,被送入医院打营养吊针。出院后,女儿“像彻底变了个人”,不爱说话,总把自己关在房间内玩手机,“饭也不吃,澡也不洗。”喊她吃饭,若她正在打游戏,便会“发狂一样地喊叫”。半年来,她在全县的成绩排名从一千多名掉到近三千名。
今年四月,文洁为女儿洗衣服时,无意中洗坏了其留在牛仔裤口袋里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同学给她的游戏账号。”女儿抄起一个凳子,摔裂了,又对着文洁大骂一些“非常脏的话”,便摔门而去了。
文洁很心碎。在她的印象里,小慧刚读小学就会扫地、擦桌、给自己煮面条吃,还会和她一起编鞋子卖,以补贴家用。文洁在农家乐做服务员,一个月只歇两天,每天端菜、清洁十几个小时,回到家往往精疲力竭,小慧会给她打水泡脚,“甚至把我脚捂在怀里取暖。”
而今,女儿变了,文洁认为,是电子游戏改变了女儿。

年轻人在网吧上网。图源IC photo
“瘾”从何来
五年前,张海宁居住的村落连入无线网络,村里的孩子逐渐“一堆一堆地”窝在各家的墙脚,“抱着手机蹭wifi。”他的儿子洋洋是什么时候加入其中的,他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儿子玩的是一种“打来打去,非常刺激”的游戏。
自两年前禁止儿子玩游戏起,他便察觉到儿子的学习专注力在逐渐下降,“以前小孩回家第一件事是做作业,现在回家磨磨蹭蹭,找到机会就要问我借手机查作业。”有几回,张海宁小睡过去,醒来已是凌晨,发现孩子依然在客厅“捧着手机写作业”。
上周,儿子提出自己考了一门一百分,想玩手机,“我老婆同意了,把手机给了他——我说你考一科一百分,就要玩手机,那么如果考两科三科呢?好好学习怎么能附带条件呢?”张海宁将手机收回,孩子“跳来跳去,大哭起来”。
张海宁总结,儿子对游戏“入迷”了。
文洁记得,大约两年前,女儿的学校因疫情的缘故开始上网课,她便把一台旧手机给女儿使用。至于女儿是否从此开始玩游戏,她未曾留意。唯一的迹象出现在去年6月,有朋友告诉她,她的微信号显示在打一款推塔类游戏,应该是她的女儿在操作。但她想着,“学校里学习累,休息的时候,玩玩就玩玩了。”便没作干涉。
直到“充钱”事发,她才发觉,从前连电视都看得不多的女儿,对游戏的“瘾”已非常大,“整天整天地想着要升级、要闯关。”
她试图询问女儿沉迷游戏的原因,女儿回答,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玩。
“游戏里面的级别、目标都非常清楚,打掉这个怪就能升一级,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实现之后不断地奖赏,能刺激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尚俊杰曾分析,人们之所以热爱玩电子游戏,是享受随之而来的生理性的刺激。
香港大学人类学博士饶一晨曾做过与“网瘾少年”相关的田野调查。他回忆,彼时他所接触的“网瘾少年”多沉迷于“高度竞争的游戏”,如枪击类游戏、推塔类游戏等等。
他说,当下许多热门游戏的设计,“利用了人类神经的弱点”,每一场游戏都给人“短、平、快”的刺激,而孩子更难抵挡这种刺激。相应地,孩子就容易陷入电子游戏无法自拔。

2021年7月28日,上海,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在一电子卖场内玩网络游戏。图源 IC photo
“其实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普遍是具备中上的认知水平的。”饶一晨说,他与“网瘾少年”们交流,发现他们多数能客观认识到自己在电子游戏上花费了过量的时间或金钱,“就是忍不住。”
他观察到,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也常是导致青少年沉迷游戏的原因之一。“许多孩子受到的教育,是必须获得好的成绩、念好的学校,才能获得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他们被迫在这样一条竞争赛道里,所得的成绩与家长与社会的期待是有差距的。所以,他们会在快速获得正向反馈的游戏世界里寻求安慰。”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曾带领团队对一万余名未成年人进行调研,她发现,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游戏态度亦有影响:在民主型的家庭环境下,孩子沉迷游戏的比例为1.7%,在专制型家庭,孩子沉迷游戏的比例为9.7%,而在放任不管型的家庭,这一数据比例则高达11.7%。
极偶尔,张海宁会与儿子交流手机游戏,“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玩游戏?他说在游戏里可以打枪、打仗,会有‘成功的喜悦’。”
但他仍自称坚决不允许儿子玩电子游戏:“即使你在游戏里有再大的成就感,你学到的东西也都是没用的。”
文洁则分析:“大概就是游戏故意设计得会让人有瘾?”这让她愤恨。采访过程中,她总是忍不住发问:为什么不禁止游戏?
“防沉迷”的二十年
实际上,中国早在二十年前便开始对青少年人群的电子游戏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从2002年起,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陆续出台有关政策,例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将未成年玩家的‘健康游戏时间’设定为3小时以内”“各网游运营商投入使用防沉迷系统”等等。
然而,最初这些尝试效果甚微。有媒体发文分析,早年,因各个游戏公司没有向公安部调取、核验身份证号与姓名的权限,政策要求建立的防沉迷系统无法做到百分百的实名制,“(未成年人)网上随便找个身份证生成器,或者找父母、亲戚、门卫大爷随便借个身份证输入一下,甚至网上还有贩卖成年人信息帮助注册账号,即可轻松跨入成人世界。”
近年来,多家互联网公司与公安部就身份认证系统达成合作,情况有所改观。
2019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提出“每日22时至次日8时,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8~16周岁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等要求。
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再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这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政策”。
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的最新报告,2021年的防沉迷新政出台后,超八成受访家长表示孩子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43%的家长称“明显减少”。另外,根据南方都市报调查问卷,去年8月的《通知》发布后,“每周玩游戏1-3个小时”的学生占比下降了4.36%,“不在网络游戏上有所花费”的学生比例,从87.06%上升到90.17%。
为配合政策,国内大型游戏公司如腾讯、网易纷纷推出家长监督平台。例如,家长们可以通过腾讯“成长守护平台”绑定孩子的游戏账号、实时监督孩子的游戏行为。有腾讯内部人士介绍,系统发现实名为成年人的账号有疑似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会在游戏登录或消费时,要求人脸识别认证;针对55岁以上实名用户的夜间登录行为,系统也会启用人脸识别,以防止未成年人冒用家长账号或设备等。
文洁在家长监督平台上将女儿小慧的游戏账号设置成了青少年模式,凡用此账号玩游戏,时长不能超过两小时。然而,今年初,她发现女儿借用了别人的账号打过一次推塔类游戏。
张海宁近来听人说了,“小孩子给游戏充钱需要人脸认证。”他的儿子洋洋再未有过电子游戏消费,也不再玩从前那款“打打杀杀”的游戏,转而玩一款“砍树、盖房子”的游戏。
他说,儿子在手机上密密麻麻装了两页应用程序,“所以我想,就算有些游戏有时间限制,但他总能找到能玩的东西。”

2021年7月28日,小朋友在商场内玩枪击类游戏。图源 IC photo
正确应对和引导
时代变了,文洁感慨。
她小的时候,与伙伴的娱乐局限于跳绳、踢毽子等活动,要不就是上镇里、县里去逛街,“连电视都很难看到。”张海宁也有同感,他童年时做的游戏,无非是下河摸鱼、玩水,或是自制两把木头手枪,扮解放军打仗。而今,他们的孩子从出生起,就沉浸在电子科技与互联网的汪洋之中。
家长们对未来充满担忧。
张海宁想,等儿子念到中学,总要给他配一台手机,“现在这是必需的工具,没手机,人就和瞎子一样。”至于后续的游戏时间管理,“只能靠孩子自觉。”
文洁则说,自己从未想过没收女儿的手机,“没收是不现实的,现在哪个孩子不玩手机?而且总要让孩子和同学在QQ上聊聊天。”她所希求的,不过是孩子能从电子世界里留出时间,“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该念的书念好。”但她心里没有主意,盼着孩子“能变得懂事”。
“孩子沉迷游戏的‘锅’不应该只甩在家长身上。家长和孩子一样,都不了解游戏的多元性、复杂性,他们通常觉得所有的游戏都是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怎么判断什么游戏是好的、是应该让孩子玩呢?”学者刘梦霏说,“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孩子彻底远离电子游戏,什么游戏也不玩。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留给家长的都是无力感。”
2015年,刘梦霏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国内第一门游戏研究课程“游戏研究与游戏化”,致力于电子游戏研究及去污名化。
“现在我们讲到电子游戏,就说是电子鸦片、电子海洛因,实际上,游戏产业是很复杂、很多元的。”刘梦霏认为,市面上的游戏可分为赌博游戏、消费游戏、作品游戏,不同类型的游戏应有不同的管理办法。
“我觉得,赌博游戏,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抽卡游戏,国家应该禁止青少年触碰,因为这种游戏的核心机制就是赌博。”刘梦霏解释,“而那些免费下载、道具收费的游戏,我归为消费游戏。它的核心是一套消费与社交系统,比如孩子在游戏里买皮肤,只是在朋友面前显得好看,但游戏能力并没有变得无敌,没有因为消费而在游戏体验上碾压其他玩家,这是消费游戏的平衡之处。所以,就像吃零食一样,孩子可以适当地玩消费游戏——但孩子也不该只玩消费游戏。”
刘梦霏认为,对孩子真正有益的是作品游戏,“一种能带来精神触动的,有知识、文化与审美表达的游戏。”她举例道,她玩过一款武侠类游戏,玩家需要学习“宫商角徵羽”的音律知识,若要在游戏里掌握医术,还需背诵一张古代的人形穴道图。又比如,她小时候常玩的一款航海系列游戏,玩家可以坐船前往地球上未知的海域,游戏中,既有“大航海时代的人物的主观能动性的表达”,也有“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学习”。每次考试前,她都会玩此游戏来整合记忆地理知识。
但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二十余年以来,市面上消费游戏、赌博游戏大行其道,真正的作品游戏已十分罕见了。因此,刘梦霏表示,在监督设置防沉迷系统之外,有关部门也应适当给予作品游戏一定的支持,“比如给更多版号、扶持建立资料馆、在更多学校开设更多游戏教育学科等等,让游戏教育和游戏研究拥有一个更正规的体系。”
“电子游戏的出现是时代潮流,我们不应该逆潮流而行。如今,要杜绝青少年接触游戏已经不可能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学校给予孩子正确的游戏教育,培养他们的游戏审美、游戏时间观、游戏消费观,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游戏是好的,什么游戏是不好的。这样,社会上所谓的网瘾问题,或许会大有改观。”刘梦霏说,这也能改变家长群体的无力局面。
另一方面,短期内,家长们用自己的方式试着改变孩子。
张海宁在家里支了张乒乓球桌,空下来就和儿子打球。他实际上是个忙人,照料着家里几亩地之外,还常常要做砍毛竹、挖竹笋、腌鱼干等活计。“孩子放假一个人在家呆半天,可能就看半天的电视,或是玩半天的手机。”他决意要多陪陪儿子。
与女儿起冲突之初,文洁整夜里睡不着觉,“想死的心都有了。”后来她查阅到网上的教程,在平台上申请退得女儿充值的三千余元。五月份,她又在平台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为女儿写了两封信,折起来放在女儿的枕头上。
她在信里折中地写道,“妈妈不要求你多的,就要求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好之后,你想休闲玩手机,你就玩吧……”
女儿回家后,读了信,与她谈了一番。第二天,她领着女儿到县里逛街,在奶茶店又深谈一番。她觉得女儿“好像是听进去一点了”。
女儿开始有些“原来的样子”,“至少愿意和我说话,愿意吃饭、洗澡,能把自己拾掇干净了。”母亲节当天,女儿送了她一张贺卡和一个发卡。发卡是金色质地的,嵌了十多颗大红珠子。文洁感到久违的宽心。

母亲节当天,女儿送了文洁一张贺卡和一个发卡。受访者供图
不过游戏是仍然在玩的。文洁说,女儿最近换了胃口,玩起一款卡通风格、跑来跑去的游戏。她对此毫不了解,女儿对她说,那是一款“冒险小游戏”。文洁遵守约定,默认了女儿的游戏权利。
5月27日,文洁接受采访的夜里9点多钟,女儿就在隔壁房间展开着她的“冒险”。
(文洁、张海宁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贾宁